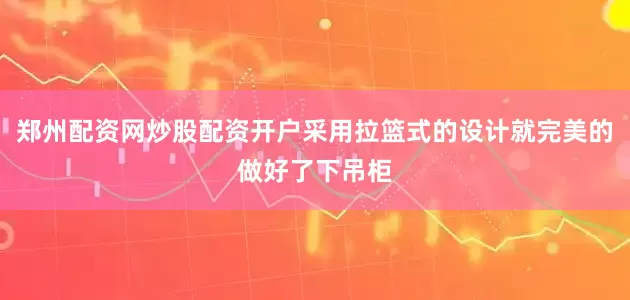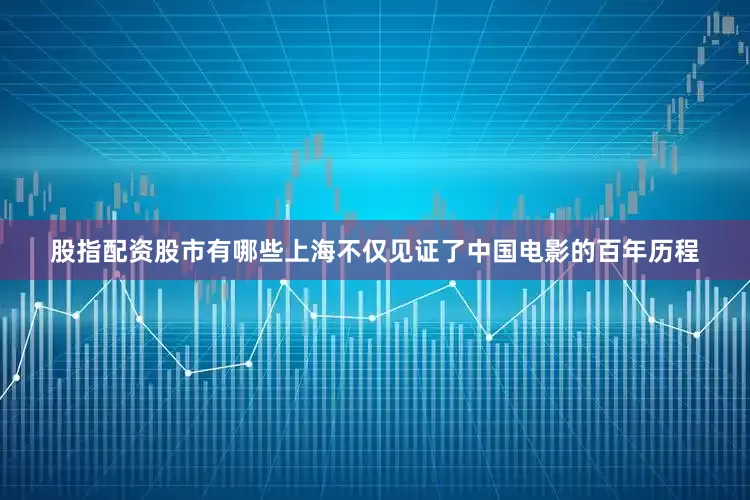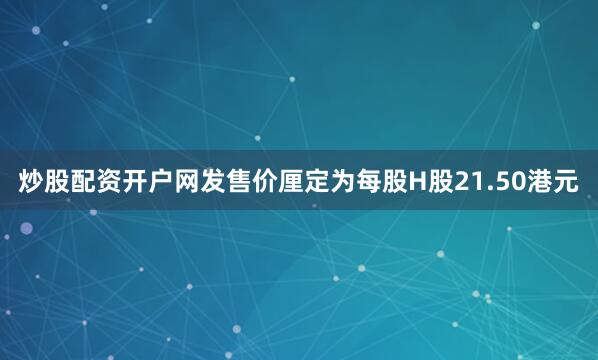美国知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着手创作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一书的征途中,特地远赴中国搜集相关资料,并与当事人及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。1984年6月15日,他拜访了李先念。李先念坦言:“关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之路,我仅略作沉思,尚未进行充分的准备。即便给我半年的时光,恐怕也难以完成全面的筹备。”
下面,我将详细描述红四方面军的创立发展史。在我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部队中,红四方面军占据一席之地,它在党的领导下,展现了非凡的战斗力和优秀的品质。那么,这支部队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呢?这一切起源于湖北与河南交界的黄麻起义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董必武实际上担任了武汉中学的校长,他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学生。正是这些学生,在黄麻起义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,这一历史细节过去并未被广泛公开。
1927年,蒋介石在“四一二”事件中背叛了革命,发动了政变,由此引发了宁汉分裂,全国范围内弥漫着白色恐怖。在湖北与河南的交界处,尤其是黄安、麻城一带,农民们纷纷揭竿而起,这一壮举被历史永远铭记为黄麻起义。若您有幸踏上鄂豫皖的土地,尤其是深入红安、麻城,定能收获丰富。尽管这次起义最终以失败收场,众多革命志士英勇牺牲,农民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屠杀。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,有人选择了消极应对,有人背离了初衷,还有人则沦为“亡命之徒”,他们决心继续投身于斗争之中。我,作为一名小手工业者,木匠,当时也沦为了所谓的“亡命之徒”。
尽管黄麻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,但参与者的数量已锐减至不足三分之一,大约仅有三百人,在最艰难的时刻甚至不足百人。然而,广大农民同胞对我们的同情之情如潮水般涌动。我们与农民同呼吸、共命运,紧密团结在一起,共同孕育出了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。

图片
毛泽东(右二),红军时期。

图片
建国后的李先念
该部队之所以能迅速扩张壮大,根本原因在于农民们正承受着沉重的压迫,这使得他们对革命的需求显得尤为急切。此外,蒋介石、桂系、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持续的混战,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良机。这场战事不仅对我们有益,而且对中央苏区的稳固与成长也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。
最早被中央委派至鄂豫皖战区的,是徐向前,而倪志亮的名字亦有所提及。彼时,徐向前身担师长重任。在湖北、河南、安徽三省交汇的农民起义军之间,联系尚显松散。徐向前抵达时,我担任副班长,班上成员仅八人。不幸的是,我们的班长郑重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,我因此接过了班长之职。那段艰难岁月中,班长有权限直接向军长汇报。鄂豫皖的红军被称作第四军,这源于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,第四军以英勇善战闻名,因此这个名字成为了我们的骄傲。后来,井冈山的红军得知我们的称号后,便将自身更名为第一军。
1931年四月,张国焘莅临鄂豫皖根据地,当时我军人数已突破两万之众。我们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,因其肩负着中央派遣的使命,身兼中央代表与军分会主席的双重要职。他带来了王明的“左”倾路线。在此之前,瞿秋白、李立三的“左”倾盲动主义错误已给根据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然而,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危害最大的,无疑是张国焘。他上任后,推行“肃反”政策,打击“改组派”。这个“改组派”由汪精卫发起,后来逐渐分化。在“肃反”的过程中,军长许继慎不幸被误杀,他曾就读于黄埔军校,同样,徐向前也是黄埔的杰出校友。黄埔军校培养出了无数优秀人才。
红四方面军西征
踏入鄂豫皖这片土地,在张国焘的英明领导下,我军英勇奋战,屡创佳绩,接连取得了黄安、商潢、苏家埠、潢光四大战役的辉煌胜利,鄂豫皖地区由此迎来了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。根据地版图迅速拓展,革命政权在二十余县得以稳固建立,红军兵力也激增至四万余人。1931年11月7日,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庄严宣告成立。
在四大战役的辉煌胜利余波未平之际,张国焘因胜利的喜悦而头脑过于膨胀,陷入了骄傲自满的泥沼。然而,蒋介石的军队却迅速发起了第四次对红军的“围剿”,主战场重新聚焦于鄂豫皖地区。黄安县城不幸失守,而我军远在战场外线,无力及时回援。正值酷暑炎炎,烈日炙烤,加之调动大军与卫立煌部决战,此战未能如愿以偿,我军被迫撤退至七里坪,再次陷入激战。战斗异常惨烈,虽然消灭了敌军两个团,但自身伤亡同样惨重。当时,我担任团政委,我团的人数锐减。于是,总指挥部果断作出决策,穿越京汉铁路,暂时撤离鄂豫皖地区。这次撤退实属无奈之举,并无既定计划。最初,我们计划先击退敌人,然后再返回原地。然而,一旦越过京汉铁路,便无法回头。敌军对我军进行阻击和侧击,我军只能向西部进发。那时,我担任十一师政治委员。最为惨烈的战斗莫过于新集之战。敌军将总指挥部团团包围,我们与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,成功解救了总部。然而,这场战斗的伤亡同样极为惨重,三位团长中有两位英勇牺牲,三位团政委中程世才受伤。
离开根据地之后,人员和物资的补给变得格外艰难。幸好,一位年轻英勇的战士加入了我们的行列。随后,我们继续向西挺进,深入陕西腹地,在此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——子午镇之战。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激战中,张国焘面临极大的险境,承受着来自两翼的猛烈夹击。我自己也身受两处创伤,至今仍有弹片残留在体内。在穿越秦岭和汉江的过程中,我不得不依靠轿夫的抬送前行。
为何决定撤离鄂豫皖?首要原因是敌军对根据地的破坏极其严重;其次,是由于在政策上出现了“左”倾偏差;此外,人力和物力的过度消耗也是一个关键因素。
在我家乡的红安县,当年的人口数量约为五十八万。然而,在那段充满硝烟的抗日战争岁月中,当我短暂返回故里时,却发现人口数量急剧减少至二十余万。在这场灾难中,每家每户都承受着失去亲人的深切悲痛。我家同样未能幸免,遭受了多重不幸的打击。三哥在战火中英勇牺牲,二哥则不幸被误解而丧命,而大哥则远赴汉口,若留在家乡,恐怕也难逃被追害的命运。四哥虽然态度消极,却并未对革命表示反对。这样的一个家庭,内部意见不一,涵盖了左、中、右的不同政治立场。
红军跋涉五千余里,终于抵达了川陕之地。蒋介石的军队对四川境内望而却步。四川境内盘踞着四位实力雄厚的军阀:刘湘、刘存厚、田颂尧、杨森,各自为政,混战不断。这些士兵普遍缺乏基本常识,竟然有人坚信枪支无法夺人性命,众多官兵沉迷于鸦片的诱惑。他们虽愿放下手中的武器,但对烟枪的依赖却难以割舍。在战场上,他们吸食鸦片后,常常将枪口高举向天,空放一枪。
在四川境内,我方兵力不过两万之众。伊始,即对田颂尧所部发动了主动攻势。田部分兵三路向我军进击,我军则展开了针对性的反三路围攻战,巧妙诱敌深入我方根据地。在空山坝一役中,我军成功挫败了田颂尧的部队。此后,以刘湘为首,调集六路兵力对我军发起了围攻。此战历时冗长。东线由徐向前、陈昌浩、许世友等将领指挥,万源保卫战期间,参战部队及人员众多。陈锡联所率部队成功击败了刘湘的军队,本可乘胜追击至长江之畔,然而,张国焘却下令停止追击。东线胜利之后,徐向前转战西线,指挥黄猫垭战役,一举歼灭了田颂尧的七个旅。
懋功会师
索尔兹伯里问:联系党中央?
李先念回应称:“这两者之间确有关联,但并非频繁发生。我们依赖电台和密码本进行通讯。至于总部与各军之间的联络,则主要依赖其他通讯方式,而非单纯依靠电台。”
嘉陵江,天然构筑的四方面军西进的坚固防线,其突破势在必行。这一决策不仅恰如其分,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军深入岷江流域,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战略布局。两个月后,在我军准备继续西进的关键时刻,徐向前将军的指令如约传来,派遣我前往迎接一方面军。我们历经艰辛,翻越了红桥雪山,成功攻克了懋功城。然而,那时我们尚不清楚一方面军的确切位置和到达的具体日期。韩东山师长作为先头部队的指挥官,曾来电通报一方面军的将至,但我起初对此持保留态度,告诫他们不可轻信敌人的诱敌之计。数日之后,我在懋功城有幸见到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彭德怀、杨尚昆、叶剑英等一众领导同志。毛泽东关切地询问我的年龄和部队当前的人马状况。当两军胜利会师,干部战士们的情绪高涨到了极点,那种激动的情绪实在难以用言语充分描绘。
索尔兹伯里问道:“您是否准备好了要赠予他们的礼物?”
李先念曾言:“我们全力以赴,为他们提供了坚实的支援,筹备了充足的粮食。那时,我国正处于国力鼎盛之时,遂派出数千人予以大力协助。”
毛泽东数日后与张国焘会合于两河口。
在两河口会议之际,分歧之音悄然响起。那时,我正驻守懋功之地。争论的焦点集中于,中央坚决主张向北拓展,意图重返岷江以东;而张国焘则倾向于西进,先取康定,再图青海——此乃一条看似不通的死路。根据中央的决策,部队向毛儿盖进发。不久,中央在沙窝和毛儿盖两地召开会议,明确了向甘南进军的战略方向。我亦参与了毛儿盖会议。军队被划分为左、右两路。右路军由中央军委、一、三军团,以及四方面军的三十军、四军组成,由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指挥。左路军则由四方面军的九军、三十一军,以及一方面军的五军团构成,由张国焘、朱德、刘伯承等负责指挥。当右路军抵达巴西时,胡宗南的四十九师紧追不舍,我们在包座将其击溃,师长亦命丧黄泉。我们缴获了大量物资,其中包括不少哈达门牌、万国牌的纸烟。同时,我们也为毛泽东及中央的其他领导送去了部分物资,如饼干、罐头等。然而,此时张国焘不愿继续北上,以噶曲河水位上涨为借口。徐向前、陈昌浩通过电报催促他率部渡河,并表示可以派遣一个团进行接应。如今,有人声称噶曲河可行,也有人认为不可。纵使河水上涨,也只是暂时的现象,稍作等待便可以渡过。然而,分歧的实质在于张国焘意图夺取权力,试图取代毛泽东的位置,企图分裂党和红军。陈昌浩亦心生动摇,不愿继续北上。最终,我们不得不再次南下,重返懋功。
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
索尔兹伯里提出了两个疑问:首先,张国焘是否曾对毛泽东构成武力威胁?其次,朱德的活动是否受到了限制,缺乏自由?
李先念回应称,针对第二个问题,他坚信其中并无实质。尽管如此,朱德将军的提议并未得到张国焘的采纳,而有些人对于朱老总的某些举措可能存在过激的反应。
关于首个问题,我目前尚无确切答案。然而,我曾注意到,在延安举行的批判张国焘的政治局会议上,毛泽东曾引用张国焘所发电报中的一句话:“南下,彻底开展党内斗争。”
彼时,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。我察觉到毛泽东对于张国焘意图篡党夺权的企图已有警觉。
索尔兹伯里认为回答合理。
李先念曾语重心长地指出,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与第三十军南征,我和徐向前、陈昌浩都肩负着相应的职责。徐向前不仅是我们队伍的领袖,更是我最亲近的朋友。他对张国焘的领导风格颇有微词。他曾向我倾吐,一方坚持南进,另一方则倾向于北上,局势显得颇为复杂。尽管面临重重困难,最终我们还是遵从了张国焘南下的命令。
南征至百丈关,历经一场激战,遗憾的是未能取胜,遂撤军至西康。那片土地荒凉,人迹罕至,偶见人烟,居民多为藏族,语言不通,日常饮食则以牛羊肉为主。
往昔,我们圆满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,有幸与二、六军团的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应、萧克、王震等杰出将领重逢,随后共同踏上了北上征程,穿越了茫茫草地。雨季已过,路况相较于前次有了显著改善,伤亡人数亦有所降低。面对藏民骑兵的突袭,我们并未与其陷入纠缠。抵达巴西后,我们着手准备越过腊子口。尽管敌军人数众多,但一经我军炮火猛烈攻击,便瞬间溃散,我军随即占领了岷县。
此刻,张国焘与陈昌浩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,这场争论令众多人感到困惑。张主张率领部队渡过洮河,向甘西进发,而陈昌浩则坚决主张先北上与党中央汇合。在这场争执中,徐向前等人并未介入。张国焘匆忙赶往前线,泪流满面地指责陈昌浩对他怀有敌意,并认为主席之位不应再由他担任。陈昌浩抵达前线后,同样情绪激动,声称若部队西进受阻,他将毫不犹豫地辞去职务。尽管我们竭力调解,但仍难免出现失误。部队一度向洮河方向行进,却发现道路不通,只得转向北方。当时张国焘内心充满忧虑,不愿与中央汇合,原因在于他企图分裂红军、分裂党。他意图与中央保持距离,试图独树一帜,继续与中央对抗。然而,这次他的阴谋未能得逞。1936年10月初,红四方面军总部抵达会宁,标志着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。
西路军
正当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际,中央政府发布了全新的战略指导与作战计划。一日,漳县突然接到总部发来的紧急电文,经专人精心解码,内容指示我立即启程前往会宁。我率领骑兵部队火速赶往总部,张国焘、徐向前、陈昌浩、李特以及朱德等领导均已齐聚一堂。他们向我出示了一份电报,那是批准我们西渡黄河的命令。我反复细读,发现电文由毛泽东与张闻天共同签署。电报阅毕,我立刻向徐向前、张国焘、陈昌浩提出了解决渡船问题的方案,毕竟缺乏船只,我们难以成功渡过黄河。现场还有几位参谋,他们告诉我黄河岸边有一片森林,可以用来打造船只。当晚,我便马不停蹄地赶往黄河边。鉴于我出身木匠世家,对何种树木适合造船有着深刻的了解。我随即向总部发出电报,告知所需树木已备齐,但缺少铁钉和麻绳,请求支援并要求集结水手和木匠的力量。若红军一方面军中有人才可调派至造船事宜,恳请予以协助。我率领的七个团已全部抵达黄河岸边,一切准备就绪,只待渡河。
因侦察员未能进行充分的侦察,我们首次尝试渡河时,船只仅抵达了沙洲的边缘。对岸的河面显得更为宽阔。于是,我们选择了返航,将船只拖至山沟,并巧妙地用泥土掩盖,幸运的是,敌人并未察觉到这一举动。次日,我与程世才化装成牧羊人进行侦察,发现了一处名为虎豹口的渡口,并成功利用此处过河。紧接着,我们便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滩头阵地争夺战,尽管付出了数十人的伤亡代价,但我们最终还是将敌人击溃。
在讨论渡河命令的来源时,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认为这一命令出自中央高层决策,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张国焘的个人指令。在我看来,红军西渡黄河与张国焘南进的战略目标有着根本的不同。中央的明显目的是为了控制宁夏地区,从而与苏联建立联系,争取外部支持。至于张国焘是否企图利用这一命令达成其他目的,这一点我并不确定。原本红军主力计划渡河,然而未能如愿的原因是敌军飞机摧毁了所有船只。
盛丰颐养园,西路军行进至凉州(今武威)、肃州(今张掖)、甘州(今酒泉)等地,局势变得愈发复杂。既无法继续向前推进,也无法转身撤退,部队在东西之间徘徊。若真的坚持西征至新疆,恐怕结局将非今日所见的这般。
我生命中最为苦涩的经历,首当其冲的是张国焘对党中央的背叛之举;紧接着,便是西路军的悲惨历程。在河西走廊,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那里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,走廊狭窄,且我军历经三次草地跋涉,疲惫不堪,弹药极其匮乏,每人仅分到五发子弹。在摄氏零下二十度,甚至三十度的极寒中,战士们仍需穿着单薄的衣物。敌军得以养精蓄锐,而我们却要在夜晚行军,每晚要行进六十里,敌人的骑兵仅需两个小时就能追上我们。在古浪的战斗中,九军损失惨重;在高台之战中,五军几乎被敌人全歼,董振堂军长也英勇牺牲。九军军长孙玉清、政委陈海松也英勇就义。陈海松的年纪甚至比我还要年轻。我们的副军长熊厚发也遭敌杀害。这支部队在河西地区孤军奋战近半年,直至1937年3月才最终失败。军队溃散,建制混乱,仅剩一个团尚能保持完整建制,人数不过二三百。整个军队剩余的人员不足两千。我们分成了三个支队,由王树声、张荣分别率领其中一个支队,而我则指挥主力部队。徐向前不愿离队,而我则衷心希望他能留下。陈昌浩将中央的电报交给我,中央命令他离去。学界精英纷纷离世,而我则留下了李卓然,他曾留学苏联,曾是方面军政治部主任,才识过人。
徐、陈两位同志离队之后,李卓然同志与王树声同志紧急召开会议。我提出,若要寻求生存,我们不得不穿越险峻的祁连山脉。然而,不幸的是,王树声同志所率领的支队不久便遭到了敌军的围剿。我们历经艰险,成功翻越了祁连山,这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。敌军踪迹渐远,我们每日行军三十里,若超过这个距离,队伍中的众人便难以继续前进,掉队的风险极高。起初,我们与中央及援西军总部失去了联系,只能依靠指南针和分省地图来确定行军方向。
抵达安西之时,我不慎犯下了一个错误。曾幻想在安西捞得一笔横财,却最终一无所获,甚至还无意中将已修复的电台损毁。当时,我们队伍中还剩900余人。安西之后是无尽的沙漠,再往前便是星星峡。就在这个时刻,陈云和滕代远同志率领的数十辆卡车前来迎接我们,苏联也伸出援手,送来了皮靴、枪械等物资。数日之后,西路军的残部约有400人抵达了迪化,也就是今日的乌鲁木齐。到了1937年底,我终于得以重返延安。
胜亿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